在這個寒冷的冬天,有一本新書的出版,迅速引爆了整個歐美世界。
它的火爆程度,堪比當年的《哈利·波特》。
它就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的妻子、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·歐巴馬(Michelle Obama)的親筆自傳《成為》(Becoming)。

還在預售的時候,它就已經登上了美國亞馬遜全榜第一名的寶座。
企鵝蘭登出版社在北美首印 180 萬冊。
僅在正式開售的第一天,就賣出了 72.5 萬冊。
在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荷蘭、西班牙、丹麥和芬蘭,《成為》都登上了非虛構類榜單的第一名。
根據出版社公布的數據,截至到目前,上市一個多月的時間,全球銷量超過 500 萬冊。
包括中文在內,這本書已經確定會翻譯成至少 28 種語言在各國陸續出版。
它刷新了 2018 年整個英文世界的圖書銷售紀錄。
美聯社評價說,《成為》是今年最受人們期待的政治類圖書。
美國脫口秀女王奧普拉·溫弗瑞逢人便誇這本新書:
「書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,甚至還有一些你想像不到的東西」。
作為米歇爾的好友,奧普拉絲毫不吝嗇她的讚美之詞:
「這本書寫得太好了,我能聽到她的聲音,想像到她的表情,感受到她的情緒。」
當我看完這本書的時候,我覺得奧普拉沒有錯,但是美聯社錯了。
因為這根本就不是一本政治類圖書。
米歇爾在書里甚至直截了當地表示:我討厭政治。
她在多年以前,就曾經多次跟歐巴馬表示:
你能不能不去從政?
你能不能不去競選美國總統?
這在今天的我們看來,都是無法理解,也是不可想像的。
她為什麼要這樣說?
這本「無關政治」的政治類回憶錄,到底講了些什麼?
為什麼米歇爾·歐巴馬恨特朗普,恨到了「咬牙切齒」的程度?
接下來你將看到的,是這本書在國內首發的中文精華解讀。
我相信,當你讀完了米歇爾的一生,你也就讀懂了你自己。
接下來,我會嘗試用第一人稱的視角,帶你走進米歇爾·歐巴馬的傳奇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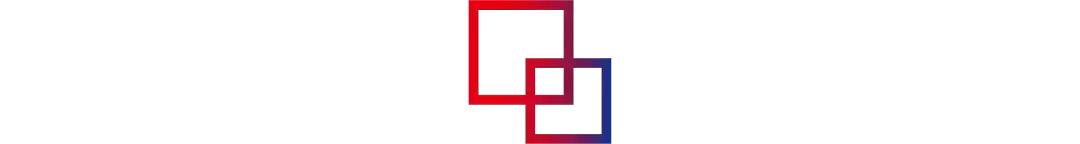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1
「我覺得你不是上普林斯頓的料兒」
1964 年,我出生在芝加哥南城的一個黑人家庭里,我們一家四口人,我還有一個哥哥。

△ 米歇爾小時候和爸媽哥哥
那時候的美國正處在震蕩之中,肯尼迪遇刺,馬丁·路德·金被人槍殺。
很多白人家庭從市中心搬到了郊區,因為那里環境更好、學校更好、房子更大、犯罪更少。
城里的白人變得越來越少。
而我們家就是留在城里的黑人家庭,我們沒有自己的房子,跟親戚住在一起。
爸爸是一個普通的藍領工人。
而媽媽早早開始教我讀書認字,她帶我去圖書館,一泡就是大半天。
所以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特別自信。
上幼兒園第一件事,老師教大家認讀一組新單詞,我摩拳擦掌,躍躍欲試。
這是一組顏色詞:
「red」「blue」「green」「black」「orange」「purple」和「white」
我很順利地念出了前面 red、blue 這些單詞,所以我念得很快。
但是念到 orange 的時候就卡了一下。
念到 white 的時候,我的腦袋就蒙了。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,滿腦子想的都是 white white white,我覺得自己特別丟人,我覺得自己好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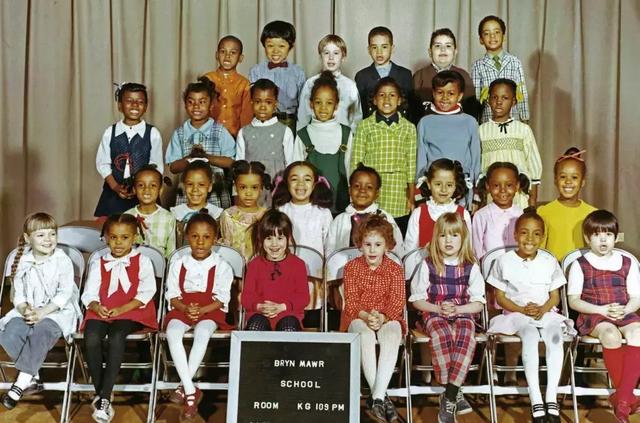
△ 米歇爾在幼兒園(三排右數第二個)
其實我心里念念不忘的,是把所有單詞全都念對的同學,老師獎給他們一人一顆金箔紙做的小星星,戴在了他們胸前。
我不甘心。
第二天上課的時候,我要求重新念一遍卡片。
老師不同意,說還有別的課要上,但我堅持要重念。
一氣呵成。
念到 white 那個單詞,我幾乎是扯著嗓子喊出來的。
那天下午,我昂首挺胸地回到家,胸前別著一枚金色的小星星。
從很小的時候,我就覺得,學習就像一場遊戲。
在遊戲中占了上風的時候,我是最高興的。
很小的時候,大人問我:長大了你要做什麼呀?
我驕傲地說:我要做一名兒科醫生(pediatrician)。
大人都說:天哪,這丫頭可真了不得!
我洋洋得意。
多年以後的我,也並沒有什麼兩樣。
小學二年級,我跳級了,因為太簡單,直接跳到了三年級。

△ 米歇爾小學五年級(第三排正中間)
到高中的時候,我考上了芝加哥還不錯的一所學校,叫惠特尼·揚高中(Whitney Young High School)。
在那里,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。
我頭一次跟很多白人子弟一塊兒上學。
因為我們那時候上學是有種族比例分配的,黑人要占到百分之多少。
一開始,我都不能確定,我是不是跟同學們一樣聰明。
在食堂打飯,認識新朋友的時候,我一直在懷疑自己:我不夠優秀,不夠優秀。
所幸我後來發現,只要我多花一些時間,我就能迎頭趕上。
我在高中幾乎是全 A 的成績。
哥哥考上了普林斯頓,所以我也想去那里。
我以排名前 10% 的優異成績,從高中畢業。
我還進入了美國國家高中榮譽生會(National Honor Society)。
但是在我申請大學之前,學校給我安排了一個專業的升學顧問做咨詢,
了解了我的情況以後,她兜頭就潑了一盆冷水:
「我覺得你不是上普林斯頓的料兒。」
我心里又犯起了嘀咕:這麼說我還不夠優秀。
那天離開那個顧問的辦公室以後,我胸口憋著一股氣,我惟一的想法就是:我要證明給你看!
我沒有顯赫的背景、過硬的推薦,努力——是我唯一能做的事。
6 個月後,普林斯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寄到了我家里。

△米歇爾在普林斯頓大學
在普林斯頓,我發現兩個特點:白人多,男生多。
男生的數量是女生的 2 倍。
而黑人才不到學生總數的 9%。
我是一個紮眼的少數派。
大學的時候,我每時每刻都在學習。
我默默地、堅定地達成一個個目標,下定決心,在每一個框框里打勾「√」。
每一次證明自己之後,還有下一次挑戰等著我。
我問自己:「我是不是足夠優秀了?」
我在意別人的眼光,我希望獲得人們的肯定。
從普林斯頓畢業以後,我又去哈佛大學的法學院,攻讀博士。
這就是我一環扣一環的童年時光和教育生涯。
我以為人生就應該都是這樣,按部就班,穩紮穩打。
直到他的出現,打翻了我人生的調色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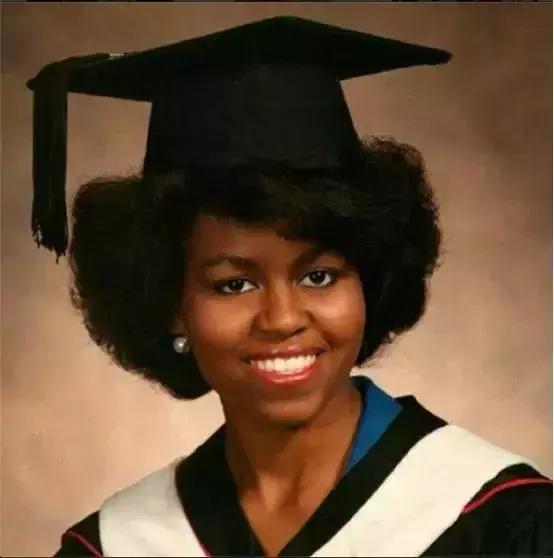
△ 米歇爾·歐巴馬哈佛畢業照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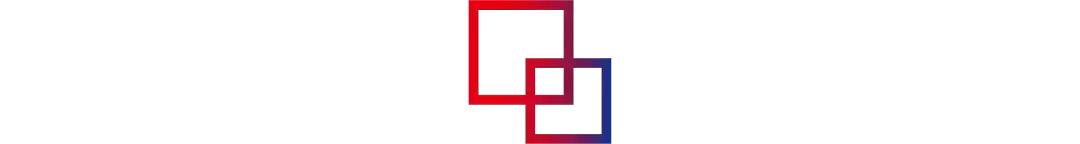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2
一個實習生,改變了我的一生
畢業以後,我順利進入了盛德律師事務所工作。
每天,我踩著高跟鞋,穿著阿瑪尼套裝,到芝加哥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樓的 47 層上班。
我加入了夢寐以求的精英群體。
25 歲,我就有了助理。
下班以後,我像很多都市白領一樣,去做有氧健身運動。
我賺的錢比爸媽一輩子賺的錢都多。
有一天,公司的高級合夥人問我:你能不能給一個馬上要來報導的暑期實習生做督導?
我說:當然可以啊。
我不知道,我的生命軌跡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同事們都說,來的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一個明星學生。
他的名字叫貝拉克·歐巴馬(Barack Obama)。

結果這個歐巴馬同學,上班第一天就遲到了。
那天下著暴雨,我還準點到了單位。
我一邊忙,一邊等他。
我問助理:「那家夥還沒來嗎?」
「親愛的,還沒來呢。」
她知道我受不了別人遲到,我覺得那樣很傲慢無禮。
同事們早都傳開了,說他剛法學院一年級結束就來了,我們盛德招實習生一般都只招二年級的。
他等於是破格錄取了。
哈佛的一位教授,也是盛德的一個合夥人的女兒說:
歐巴馬是她遇到過的最有才華的法學院學生。
還有面試他的秘書也說:他人長得很帥。
我嚴重懷疑他們所說的一切。
我看過他簡歷上的大頭照,呆頭呆腦的,長得也一般,笑的時候咧著一口大白牙。

過了十分鐘,他到了前台,我去接他,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,比我想像得要高一些、瘦一些。
(當然我也有 1 米 8 的大個兒呢。)
他知道自己是頂著天才的名聲來的,但他倒也沒有恃才傲物的勁頭兒。
我帶他參觀了公司。作為他的督導,我的職責就是給他提供建議,讓他在這兒有歸屬感。
只不過他比我大三歲,我發現他也不需要什麼建議,他在工作上很嫻熟。
但他並不是像我這樣,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。
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以後,工作了幾年,才考的哈佛研究生。
我覺得這種規劃非常隨性,像是人生路上的即興穿梭。
這跟他漂泊不定的家世背景也有關係。
他爸爸是肯亞的黑人,早年因為車禍去世。媽媽是美國的白人。
他在夏威夷出生,又在印尼生活了 4 年,在洛杉磯讀了兩年書,又轉學到哥倫比亞。
在上哈佛研究生之前,他在一家非營利組織里,做社區工作者,幫助重建社區、創造就業,年薪只有 12000 美元。
他去上法學院,是因為基層的工作讓他看到:重大的社會變革,不僅需要基層人員的工作,還需要更強大的政策,和政府的行動。
我發現我也開始有點崇拜他了,崇拜他的那份自信,還有認真。
不過我可從來沒把他看成是約會對象。
有一天吃完午飯,我發現他還抽煙——我可非常討厭抽煙的人。
在我心里,我想他也就是——我帶過的一個很優秀的暑期實習生,僅此而已。
我要把事業放在第一位。

接下來的幾周里,他每天下午晚些時候,都會來我辦公室坐坐,跟我聊會兒天。
畢竟律所里 400 多個律師,只有 5 個律師是黑人,所以我覺得還挺正常的。
不管我承不承認,我們的關係都在發生微妙的變化。
當我工作太忙,跟他見不上面的時候,我都會想到:他在做什麼呢?
如果他沒有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門口,我多少會有些失望。
我對他有感覺,但這種感覺被我隱藏了起來,藏得很深。
我不允許我的事業和生活出現任何變數,我要穩步前進,因為再過幾年我就可以做到合夥人的級別了。
或許我可以假裝忽略:我們之間正在萌發、滋長的感覺。
但他可沒有「假裝忽略」這一點。
有一天吃午飯的時候,他跟我說:「我覺得我們應該約會。」
「什麼,你跟我?」我假裝震驚的樣子——你怎麼會這麼想呢?
「我告訴過你,我不打算約會,而且我是你的督導。」
他苦笑了一下:「這算什麼理由,你又不是我的老板。」
「而且你很漂亮。」
那年夏天,事務所給我們組織了一些活動,有一天晚上,去附近的一個劇院看音樂劇《悲慘世界》。
我給我們倆報了名,督導帶著實習生去,挺正常的。
結果那天的演出非常糟糕,讓我感覺如坐針氈。
我倆苦笑地對視了一眼。
他直起身來:「咱們出去怎麼樣?我們可以現在就走。」
其實我是個一向做事有始有終的人,只是那天我不知道為什麼,我跟著他溜出了劇院。
我們倆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吧。
兩天以後,我跟他去參加了一個燒烤派對。
我看著他跟一些男同事打起了籃球,我假裝跟旁邊同事的妻子講話,有一搭沒一搭的,可我的眼睛一直盯著他。
我看著他在場上矯健的身影,我的心里第一次被他這個人……打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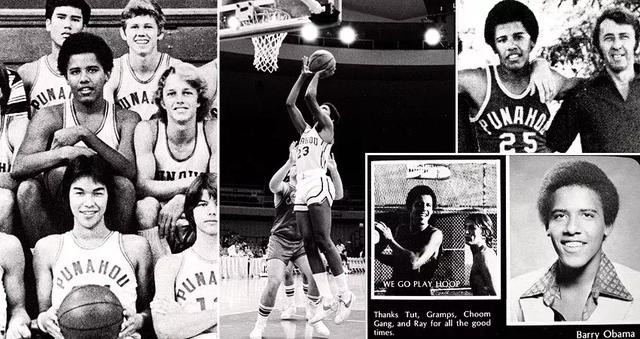
那天晚上,我們開車回到市區,我內心里感受到一種新的疼痛,一顆新播下的種子,它渴望破土而出,渴望發芽。
那是 7 月份的盛夏,而他 8 月份實習結束就要走了。
一股暖流在我的脊背上蔓延開。我在心里和自己作鬥爭。
我是不是可以,試著跟他交往一下?
我沒有把握,我不知道怎麼做才合適。
可我突然覺得,我不想再等到什麼都有把握了。
車子開進了小區,我腦袋還是有點懵。我們都等著對方說「再見」。
他抬起頭看著我。
「我們去吃個冰淇淋吧。」
他家旁邊有一個冰淇淋店,我們要了兩個甜筒,在步行街上找了個地方。
我們伸直了膝蓋,挨近了坐著。
在外頭轉悠了一天,雖然很累,但是很開心。
我們吃著,沒有說話,擔心冰淇淋化掉。
我不知道,他可能看出來我的內心已經開始松動了。
他好奇地看著我,臉上掛著一絲微笑:
「我能吻你嗎?」
就這樣,我把身體靠了過去。
一切都變得明朗起來。(Everything felt clear.)。
△ 歐巴馬夫婦年輕的時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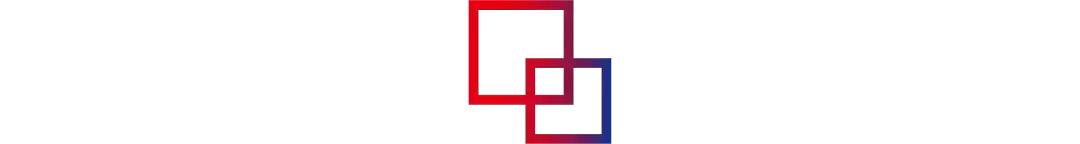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3
歐巴馬你個大騙子
貝拉克·歐巴馬是一個超級愛讀書的人。
他對物質方面沒什麼要求,他的錢基本都花在書上。
啃那些文學、哲學類的大部頭,對他來說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。
他每天都要看好幾份報紙,關注各種時事動向。
而我們住的地方離街面很近,晚上有各種吵鬧聲。
我覺得聽著很鬧心,他不覺得有什麼,他能安之若素。
有一天睡了一會兒,我醒過來,我發現他正盯著天花板發呆,他的輪廓被外面的街燈照亮了。
我說:親愛的,你在想什麼呢?
他轉過頭來,看著我,笑容有點靦腆:
哦,我剛在想收入不平等的問題。
我:……
後來我知道了,他喜歡思考那些抽象的、宏大的問題,他總覺得自己能為這些問題做些什麼。
他確實是個很「別致」的男人。
他第一次到我們家見我爸媽的時候,爸爸就很欣賞他。
只是他們覺得小夥子太優秀了,沒敢抱什麼奢望。
後來我哥哥告訴我,我倆走了以後,爸爸搖搖頭,笑了起來:
「小夥子人是挺不錯的。可惜長不了。」
他確實有一種魅力,就是志存高遠。
就像當年他在我身邊做實習生一樣,在工作中,我看得到他的謙卑,還有他願意為了更宏大的目標,犧牲自己的需求。
打球的時候,我哥哥說:「他不霸著球,但他是個有膽識的人。」
他是《哈佛法律評論》期刊,創刊 130 年來,第一個黑人主席。

畢業以後,他本可以頂著「明星實習生」的光環,到盛德這樣薪水豐厚的律所工作,但他沒有這麼做。
他有著強烈的使命感,他在芝加哥主持選民登記運動,為一家民權律師事務所工作。
這讓他還清學生貸款的時間延長了 2 倍。
他還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擔任憲法講師。
他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篤定。
而他強烈的使命感,一直在無形中拷問著我:
因為我對未來的人生感到無比的迷茫。
我討厭做律師,我不適合這份工作,雖然我能把它做好,雖然所有人都認可我。
但是它讓我覺得空虛。
我在這條路上狂奔著追求卓越,可我都沒有注意到:
我可能選錯了路。
我的熱情在哪兒?我怎麼把熱情和有意義的工作結合起來?
我害怕漫無目的的掙扎。
我想要活得像一個完完整整的人。(I wanted to feel whole.)
可我又渴望立馬得到別人的尊重、得體的收入。
我幾乎沒怎麼認真思考,就進入了法律行業。
我在想:我還能做什麼?我還有什麼技能?
而就在我迷茫的過程中,父親因病去世了,他走的時候才 55 歲。
我最好的閨蜜蘇珊娜因為癌症去世了,她離開的時候只有 26 歲。
我告訴自己:我不能浪費生命。我該行動起來了。
我面試了很多地方,歐巴馬也鼓勵我做各種各樣的嘗試。
1991 年,我開始在芝加哥市政府的公共部門就職,擔任市長助理,同時擔任規劃發展的助理專員。
那一年,他的司法考試通過了,我們去下館子慶祝。
吃著吃著,我們就聊起了婚姻的話題。
他握著我的手,說他全心全意地愛我,但他看不到結婚有什麼意義。
從夏威夷開始,他的生活就一直過得很灑脫、很隨性。他不想被什麼東西束縛著。
聽到他這些話,我頓時就氣不打一處來。
我說:「如果我們彼此相愛,為什麼我們不能用婚姻的形式確定下來?你的尊嚴會受到什麼損害嗎?」
我們總是為這個問題爭來爭去。
每次他一提這個我就火大。

服務生把飯後的甜點端了上來,
我情緒太激動了,根本沒心情吃什麼甜點。
他把盤子放在我面前,揭開了蓋子。
結果我低頭一看,本來應該裝巧克力蛋糕的盤子里,放著一個黑色的天鵝絨盒子,里頭是一枚鑽戒。
我抬頭看著貝拉克,他調皮地看著我。
他在搞惡作劇,故意逗我生氣。
我反應了好一會兒才轉怒為喜。
接下來的事情就很老套了:單膝跪地,求婚,我願意,餐廳里所有人都在為我們鼓掌。
我呆呆地看著手上的戒指。
他說:「好了,這下你該安靜了。」
你個大騙子。
1992 年 10 月,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六,我們結婚了。
我的名字,也從米歇爾·羅賓遜,變成了米歇爾·歐巴馬。

04
為了我,你可以不從政嗎?
沒錯,當他決定從政的時候,我心里是一百個不樂意。
我不喜歡政客,我也不願意讓我的丈夫成為一名政客。
我總覺得一個好人,有很多方式來發揮影響,為什麼一定要從政?
可是我反過來想:我自己不想幹律師的時候,我身邊只有他一個人支持我,鼓勵我往前走。
他從來沒有過一次,懷疑我的直覺,我的能力。
他總對我說一句話:別擔心,你可以做到,我們會想出辦法的。(Don’t worry. You can do this. We’ll figure it out.)
所以他第一次想要競選公職的時候,我同意了。
但我給他潑冷水說:「我覺得你會受挫的。」(I think you’ll be frustrated.)
「如果你最後當選了,到頭來付出多少努力,卻什麼事兒也幹不成,你會瘋掉的。」
他聳聳肩說:「或許吧。但也許我也能做點事情。誰知道呢?」
對啊,誰知道呢?
他就是這麼樂觀。
事實證明,他對了。
1996 年,貝拉克被選入伊利諾伊州參議院。

他忙到我跟他也一周好幾天都見不著面。
這期間,我好不容易懷了孕,結果沒過幾周就流產了。
後來,我通過人工授精的方式,生下了我的兩個女兒:
1998 年,瑪利亞出生;
2001 年,薩沙出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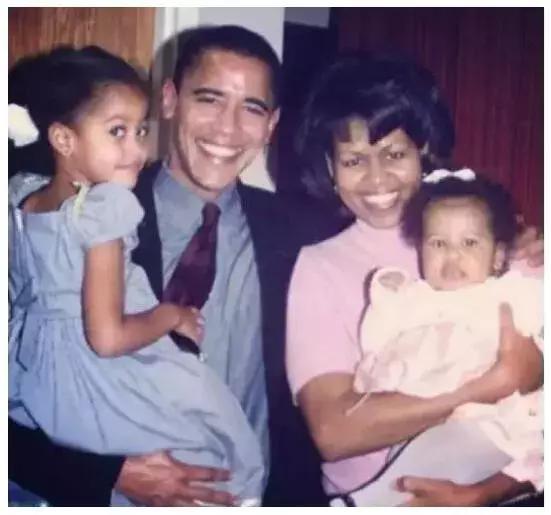
△ 一家四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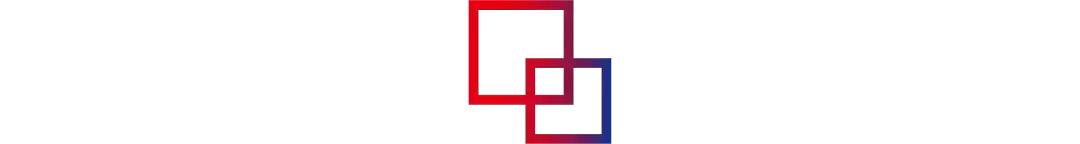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5
因為我,他敗了
我一邊工作,一邊帶孩子,我也指不上他。
因為他的事業正發展得順風順水。
瑪利亞出生幾個月後,他再次選入州參議員。
他在考慮更高的目標:進入美國國會。
如果有機會讓他在更廣闊的舞台上發揮影響力,他一定不會待在原地的。
在他競選國會議員的 6 個月時間里,他待在家里陪我和瑪利亞的時間,加起來不超過 4 天。
我心里其實想說:他沒戲,他在美國政壇上只是個無名小卒。
但我萬沒想到,他失敗的原因是我一手造成的。
那年聖誕節,我們去夏威夷度假。

突然州政府打來電話,參議院臨時決定開會,對一個打擊犯罪的法案開始投票。
任何一個參議員不到場,法案可能就沒法通過。
可是沒想到,瑪利亞半夜突然發起了高燒。
白天還在踢浪花的小姑娘,晚上就病倒了,吃藥也不退燒,她一直在撓耳朵,我覺得是耳部感染。
她這個樣子根本沒辦法上飛機。
我說:「我們還要再改簽。」
他說:「我知道。」
我有一句話始終沒有說出口:你可以一個人走啊。
他可以把我們娘兒倆扔在這兒,去投票。
我就不說,我偏不說,我看著孩子那麼難受,我心疼。
我不想讓我自己受苦。
萬一她燒得更厲害了呢?萬一得住院呢?
你會離開我們嗎?
事實證明,他沒有。他所有心思都放到了女兒身上。
後來確診瑪利亞是耳部重度感染,用了抗生素以後才開始好轉。

△ 歐巴馬和女兒瑪利亞
當我們飛回芝加哥的時候,貝拉克面臨的是一場政治災難。
打擊犯罪的法案差五票,最終沒有通過。
雖然也不差他這一票,但他因為沒有趕回來,受到所有人的抨擊。
有一位著名的議員,幾個月前剛剛在一次槍擊案中失去了親人。
而貝拉克·歐巴馬竟然為了度假享樂,不肯屈尊回來為控制槍支這麼重要的事情投票。
芝加哥的報紙上說,沒回來投票的人,都是「沒膽子的綿羊」(gutless sheep)。
有一個議員甚至點名貝拉克說:「拿孩子當借口不來工作的人,那人品可想而知。」
就這樣,因為孩子耳朵疼,貝拉克在參議院兢兢業業工作三年的成果——幫窮人減稅、幫老年人減少處方藥的費用……似乎都一筆勾銷了。
面對指責,貝拉克沒有埋怨我們,他只是平靜地告訴人們:
「我曾經聽很多從政的人大談家庭價值觀的重要性。我希望你們能理解,你們的參議員是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,來踐行這些價值觀。」
當他競選的時候,他的對手就對黑人選民到處說:
「貝拉克在我們這兒,不過是一個長著黑人臉的白人罷了。」

甚至還有著名的黑人議員公開說:
「他上了哈佛,他成了一個受過教育的蠢貨(educated fool)。我們不歡迎這些精英大學畢業的家夥。」
可我在想:黑人父母們天天期盼著自己的孩子有出息,希望他們成為的樣子,不就是貝拉克這樣的嗎?
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,努力為自己所代表的黑人群體服務。
而為了競爭選票,這些黑人議員竟然就可以顛倒黑白,說這麼「優秀」的人非我族類,其心必異。
我覺得這一切都很惡心。(It made me sick.)
我只慶幸一件事:貝拉克他關心我們,他心里有我們。
而他付出的代價就是:在民主黨初選中落敗,而那個詆毀他的對手獲得了勝利。
2001 年,薩沙出生以後,我換了一份工作,我去了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,負責社區和對外事務。
我需要更好地負擔起兩個孩子的生活開支。

△ 米歇爾在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工作
而貝拉克繼續一邊教書,一邊做立法工作。
他在醞釀下一次騰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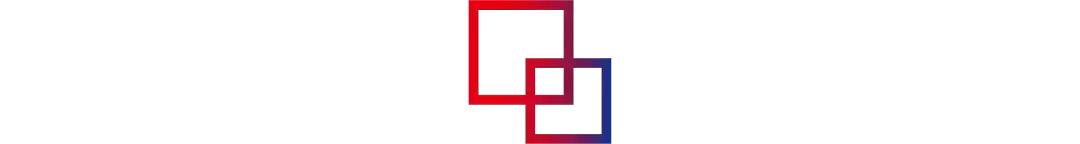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6
如果這次再敗
你必須退出政壇
他要競選美國參議院的席位。
而我們的家庭已經疲憊不堪。
我是一個需要別人的人,我需要從他人身上汲取力量,從小就是。
小時候,爸爸,媽媽,哥哥和我,就像一個正方形的四個角,我們每天都有說不完的話。
可我一個人帶著兩個那麼小的女兒,他卻三天兩頭地不著家的時候,我真的要崩潰了。
我們開始經常性地大吵。
當我看到身邊其他朋友接連面臨婚姻解體的時候,我希望我能保護我們的婚姻。
我硬拉著他,去做了婚姻咨詢。我希望我們能好好地聊一聊。
經過一段時間的咨詢以後,我覺得我們的關係有了不小的改善。
我做了一個決定:我和女兒不再無休止地等著他回家吃飯。
我們告訴他:每天晚飯 6:30,我們不等你,是你要趕上我們才行。
我們不再圍著他轉,他的工作不可以成為這個家的黑洞。
他應該是我們一家人的太陽,只不過他還想照亮更多的人。
2004 年,他再一次競選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席位。

我給他下了最後通牒:如果這次他再敗了,他就必須徹底退出政界,再找一份新的工作,了結掉這一切。
不過這次,老天爺沒有再給他使絆子,而是破天荒地給他開了一串兒綠燈。
有的議員決定,不再謀求連任;
有的比他票多的人,卷入了跟前妻的醜聞當中。
所以離選舉還有好幾個月的時候,他連一個共和黨對手都沒有了。
而他也從上一次失敗中學到了很多,在民主黨內的初選中擊敗了 7 個對手,贏得了提名。
他通往參議院的道路上,似乎鋪滿了幸運草。
而更關鍵的是,有貴人出手,把他往更大的舞台上推了一把。
2004 年,跟小布什競爭總統的是民主黨候選人約翰·克里(John Kerry),
他邀請貝拉克,在 2004 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。
在波士頓集會現場,有超過 15000 人,還有黃金時段的電視直播。
那一天,是 2004 年 7 月 27 號,他上台講了 17 分鐘,
那是我的男人在億萬觀眾面前第一次,閃耀著光芒的時候。

△ 歐巴馬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
當他說完最後一個詞的時候,台下是山呼海嘯、震耳欲聾的喝彩與掌聲。
就在那一刻,我意識到:我的男人,他不只屬於我和兩個女兒了。
他再也不會回頭了。
整件事情的經過,都讓我感覺特別不真實。
有媒體評論說:「我剛剛看到了第一位黑人總統。」
脫口秀女王奧普拉·溫弗瑞風風火火地出現在我家,花了一整天時間採訪我們。
11 月,他被選入美國參議院,贏得全州上下 70% 的選票,就連白人都開始逐漸認可他了。
有人邀請我參加一個什麼華盛頓夫人群,說里面都是頭面人物的妻子,被我拒絕了。
我的丈夫是一個參議員,可是不知道為什麼,很多人都推著他,希望他百尺竿頭,更進一步。
大女兒瑪利亞當時正在上小學一年級,有一天她問爸爸:
「你要競選總統嗎?你不覺得,或許你應該先當個副總統,或者別的什麼嗎?」
我同意瑪利亞的看法:飯得一口一口吃。
但是政治的車輪滾滾向前,我們娘倆說了可不算。

△ 米歇爾和兩個女兒
2005 年,卡特里娜颶風,1800 多人死亡,50 多萬人無家可歸。
他去到災區現場,他總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。
2006 年,他的新書《無畏的希望》出版,給他帶來很大的聲望和曝光率。
有人做了民意調查,列出了心目中的總統候選人,除了希拉蕊·克林頓,還有貝拉克·歐巴馬。
他正在認真地考慮參選。
而我希望他能謹慎一些,等時機成熟,等女兒長大,或許等到 2016 年也不遲啊。
我希望他能滿足於現在的生活,可從我認識他那天起,他的目光就一直盯著遠方,盯著他對世界的願景。
有時候,當我感受到他的不滿足,我就會很傷心。
我們結婚 11 年,我經歷了他 5 場競選,每一次都讓我覺得,這條路越發地泥濘難行。
有一天我在一家超市門口排隊,我看到貨架上《時代周刊》的封面,我立刻把臉扭了過去。
那是我丈夫的臉,旁邊的大標題寫著:「為什麼貝拉克·歐巴馬可能會成為下一任總統?」(Why Barack Obama Could Be the Next President?)

《紐約時報》甚至發表了一篇直接催促他競選的文章,題目叫《上吧,貝拉克,上吧!》(Run, Barack, Run.)
貝拉克在華盛頓的那些晚上,我一個人躺在床上,感覺自己好像在對抗全世界。
就連我哥哥都勸我:「如果他有機會的話,他就得抓住,你明白的,對吧?」
是的,我愛上了一個有遠見的男人。
他樂觀,但他不天真,他在尖銳的衝突矛盾面前無所畏懼,世界的複雜性令他著迷。
有一天晚上,他問我:「我們可以應付得了的,對吧?」
「我們不比誰弱,我們倆還這麼聰明。我們沒事兒的,我們扛得住。」

是的,當我看到電視上,卡特里娜颶風給人們帶來的滅頂之災——
我看到有的父母把孩子高舉過頭頂,自己浸泡在洪水里;
我看著多少黑人家庭在體育館里避難,掙扎著度過難捱的日日夜夜。
我在醫學中心的工作,讓我知道有多少百姓,連基本的醫保和住房都沒有保障;
貝拉克這麼多年在基層,見過多少失業工人、退伍軍人,努力克服終身的殘疾,想要走進社會;
多少母親跟他抱怨,把孩子送到了一個糟糕透頂的學校,後悔不已。
我知道,我們的肩上有一種東西,叫責任。
我知道,我沒的選,我必須接受。
那就索性打開大門,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迎進來吧!
我同意了,因為我愛他,我相信他會是一個好總統。
但我也很確定,他不會走到最後。
他有的是高遠的理想,我看到的是冷峻的現實。
貝拉克·歐巴馬,一個黑人,我真的不認為他會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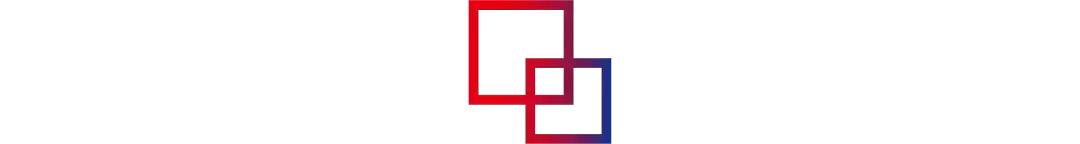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7
競選,就像逃難一樣
2007 年 2月 10 號,一個寒冬的早晨,貝拉克·歐巴馬正式宣布參選美國總統。
作為一個黑人候選人,他不能有任何的失誤,所有事情都要付出雙倍的努力。
我跟著他在各個城市奔波,我的任務看上去也更簡單一些:
講述我自己真實的故事,一個芝加哥南城長大的,四口之家的小女孩的故事。

△ 競選時的亮相
競選,並不是什麼高大上的事情,
每次活動結束,我從人群中穿過,有很多熱情的陌生人,他們會抓我的手,摸我的頭髮,把筆啊、照相機啊,甚至是孩子啊都塞給我。
我要微笑、握手,同時還要往前走。
我臉上有口紅印,衣服上有手印,整個人就像剛從山洞里走出來的女瘋子一樣。
因為行程倉促緊急,我曾經吃過很多不衛生的路邊攤。
後來長了記性以後,就改吃漢堡包了。
我訓練自己少喝水,因為路上幾乎沒有時間去上廁所。
晚上睡的旅館,有時候就在高速路旁,我要能聽著長途卡車的轟隆聲入睡,第二天依舊精神抖擻。

△ 競選中的小憩
就這樣全國各地奔波了一大圈,貝拉克還是落後他的對手——希拉蕊·克林頓 15 到 20 個百分點。
直到民主黨舉辦的「傑斐遜-傑克遜紀念日」,那是民主黨的重要儀式。
那天,希拉蕊得了重感冒。
而貝拉克最後一個發言,他再一次用「改變」征服了觀眾。
那天之後,他在民意調查中一下躍居到首位。
改變,原來真的是有可能的。

△ 奧馬巴在「傑斐遜-傑克遜紀念日」上發言
到了投票的那一天,我想結果終於要來了。
我給薩沙和瑪利亞穿戴整齊——即便是大選當天,我還是要送她倆去上學。
當我們經過無數的攝影師、錄影機,進入體育館,
當我聽到周圍的人都在說,這件事情具有多麼重大的歷史意義的時候,
我只是在心里暗自慶幸:嗯我給她倆的中午飯都裝在書包里了。
我想這是萬里長征的最後一步了。
那天,我盯著我丈夫的名字,那個長方形的按鍵盯了好一會兒。
他看著我笑了:「這位女士,你還沒想好選誰嗎?你還要再考慮一會兒嗎?」
不用再考慮了,因為全美國的人都已經考慮好了。
晚上,媒體宣布:貝拉克·侯賽因·歐巴馬當選美利堅合眾國第 44 任總統。
我的感覺就像是做夢,像個旁觀者一樣,看著我自己,麻木地做出反應。
我們贏了。

△ 總統就職儀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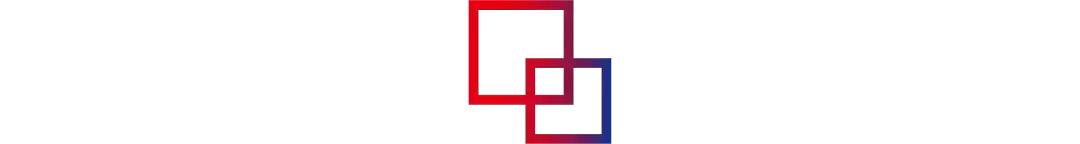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8
夫人不是你想當
想當就能當
很多人好奇地問我:做第一夫人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?
我只能說:你看籠子里的金絲雀,你覺得她快不快樂?
白宮確實是一個漂亮、舒適的地方,但它更像是一個堡壘,只不過偽裝成了家的樣子。

△ 歐巴馬夫婦與兩個女兒和米歇爾母親在白宮
舒適的意思是:在任何「小事情」上,我連手指頭都不用動一動。
外出活動有人幫我踩點兒,現場活動時間精確到分鐘,包括上廁所的時間;
帶孩子玩兒有專門的特工負責;
收衣服、洗衣服有保潔人員;
現金、鑰匙不用我想著帶,電話不用我自己接,都是助理負責。
而在總統身邊,配置進一步升級:
有 6 人團隊,負責整理當天的各種簡報、資訊;
有足足 50 個工作人員,每天專門幫他接收、回復日常郵件;
有一幫廚師,還有一幫採購員,負責食品工作,
他們會匿名潛入不同的商場,挑選我們需要的東西。
不過順便說,我們買的所有東西,都要自己付錢,哪怕是一卷衛生紙。
只有房租、水電和人員薪水,是不需要我們來付的。
有時候貝拉克早上說有一種外國水果不錯,晚飯的時候又覺得這種壽司好吃,
白宮的米其林大廚就會立馬記下來,放到菜單里,定期輪換。
大廚不要錢,可菜要錢啊。
有些食物都是專門從國外運輸過來的,價格非常昂貴,結果都是我們自己買單。
如果你見識過美國總統的車隊,你應該知道,整個隊伍至少有 20 輛車那麼長。

警車、越野車、豪華裝甲轎車、防震減災卡車、救護車、偵察車、警察護衛隊……
這是我看得見的,還有看不見的:
在貝拉克活動的周圍,有一架專用直升機隨時待命,準備帶他撤離;
在他出行周圍的屋頂上,一定有神槍手埋伏;
他身邊有一位專人醫生,車上儲存著跟他血型一致的血液,以防萬一他需要輸血。
而那輛所謂的豪華轎車,其實是一輛 7 噸重的坦克。
我「有幸」坐在這樣的車隊里跟他一起出行。
我們一家就像生活在氣泡里,跟世俗生活完全隔絕了。

△ 特工寸步不離
一旦我們涉足「塵世」,就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。
比方說小女兒薩沙去參加同學的生日聚會,特工會先去人家家里,做一番地毯式的安全檢查。
別人家家長送孩子過來的時候,特工一上來就要人家報上自己的社會保障號碼(類似於身份證號)。
搞得家長們都很尷尬,所幸孩子們倒是不在乎。

△ 小女兒薩沙坐在防彈車里
但只要是我們夫婦倆所到之處,正常的秩序都會被打亂。
有一次我們去百老匯看一場演出,開演幾個小時之前,警察就封鎖了整個街區。
所有看戲的人都要額外排隊過安檢,甚至演出都因為安檢,推遲了 45 分鐘才開演。
我當時就知道,我們倆下一次這麼「約會」,可能得是很久很久以後了。
而我們還沒到家,共和黨就已經召開新聞發布會,說我們倆這次約會奢靡浪費、勞民傷財。
每一次,我們倆出去看個戲、吃個飯,都有一堆政敵等著扒我們的料。
我們要一直生活在反對派的聚光燈底下。
所以我們的自由行動是嚴重受到限制的。
有時候我呆在白宮,想去陽台上坐一坐,但想了一下就放棄了。
雖然我只是喝杯茶,透口氣,但是會給特工處帶來很多麻煩。
因為陽台上站的人,是可以直接暴露在白宮之外的街道上的。

△ 一家四口在總統辦公室
不光是有一幫人來操心我的安全,他們怕出紕漏。
連我自己也得小心翼翼、戰戰兢兢地過日子。
有一次我們去英國拜訪伊麗莎白女王,我跟她站在了一起。

她抬頭望著我:「你個子可真高。」
我說:「是呀,這鞋根兒就高,而且我本來個兒也挺高的。」
女王低頭看了看我的黑色高跟鞋,搖了搖頭。
「這種鞋穿起來很不舒服,對吧?你瞅瞅我這個。」她也一樣。
所以我就承認了,我的腳確實很疼。
我們兩個被鞋子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女人,笑出了聲兒來
想到這兒,我不禁伸出一只胳膊,親切地摟住了她的肩膀。

我就是這樣的人,每當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,覺得投緣,我就會情不自禁地表達我的情感。
結果媒體立馬就開始罵我了,說我亂了英國王室的規矩。
因為英國王室是不能觸碰的,這是禁忌。
媒體說我粗野無禮,配不上美國第一夫人的優雅之名。
我真害怕當時我的舉動,掩蓋了貝拉克這次出訪的所有成果。
不過我那時候就在想:女王自己也覺得這事兒無所謂。
我摟她的時候,她還靠過來一些,把一只手輕輕地放在了我的後腰上。
後來英國王室還聲明說,我沒有觸犯他們任何禁忌。
我嘆了口氣。
有時候,我感覺自己得像湖面上的一只天鵝,
我工作的一部分,就是要高貴優雅地向前滑行。
但同時在水下,我的兩只腳永遠不能停止滑動。
有一年,我想給自己剪個有瀏海兒的髮型,

可我的工作人員說,我應該先得到歐巴馬幕僚們的同意,確保我剪這個瀏海兒,不會惹出任何麻煩。
我的頭髮都不是我的,真是太荒唐了。
除了髮型要管,我還要準備好一件適合參加葬禮的服裝。
因為有時候,我們會毫無徵兆地突然去參加某個士兵、議員、主管人的告別儀式。
我絲毫都不敢懈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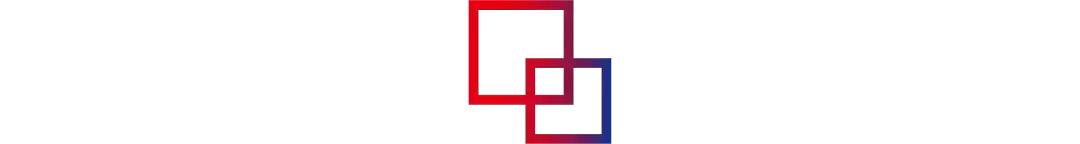
09
特朗普,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
轉眼到了 2011 年冬天,貝拉克·歐巴馬還在謀求 2012 年的總統連任,
當時還是紐約房地產開發商的特朗普,就宣稱要爭取 2012 年的共和黨總統選舉提名。
他說:歐巴馬出生在夏威夷就是一個騙局,實際上出生在肯亞。
他公然質疑歐巴馬的美國公民身份。
而媒體為了吸引眼球,不斷地為他毫無根據的猜測煽風點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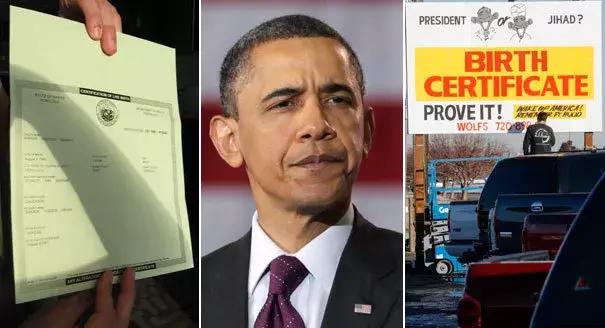
整件事讓我覺得非常瘋狂,也非常卑鄙,
他想煽動不知情的人對我們產生仇視心理。
特工處一次又一次向我們匯報,接下來可能出現的嚴重威脅。
我不可能不擔心:萬一有人聽信了謠言,持槍來到華盛頓怎麼辦?
如果這個人直接去找我們的女兒,會出現什麼情況?
沒過多久,11 月一個周五的晚上,有關貝拉克身世的謠言愈演愈烈。
一個陌生男子把車停在離白宮 800 米的街上,掏出一把半自動步槍,朝著白宮上面兩層開火。
一枚子彈擊中了一扇窗戶的玻璃,另一枚子彈射進了窗框里,其他的打在了屋頂上。
而那間屋子正是我平時喜歡喝茶的地方。
還好那天沒有人傷亡。
而唐納德·特朗普,就因為他毫無根據的污蔑,把我們一家人置於危險的境地。
就沖這一點,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他。(For this, I’d never forgive him.)

到了 2012 年總統大選的時候,很多民調結果顯示,歐巴馬的支持率和對手羅姆尼相比,只是微微領先。
而且他還在一次電視辯論中發揮失常了。
所以很多人都擔心,歐巴馬能不能連任成功。
到投票結果公布的那一天,我緊張到頭疼,我都不敢看新聞。
我突然覺得這次很可能是壞消息。
初步結果公布的時候,我拿起我的手機,給競選團隊的好幾個人發了郵件,
我等啊等啊,手機一點響動都沒有。
我覺得我的心理防線開始坍塌,各種懷疑紛至沓來:
或許是我們努力得還不夠,或許我們不配再給美國公民服務下一屆了……
我的雙手開始顫抖起來。
我焦慮得快要失去知覺了,這時候貝拉克上樓來了。
他咧著嘴笑著說:「我們把對手打得片甲不留。」
他看我一臉懵,毫不知情的樣子,馬上補了一句:「沒有任何懸念了。」
原來,樓下所有人都喜氣洋洋的。

△ 米歇爾和競選團隊
只有我,因為樓上的手機服務不知道為什麼中斷了,郵件都沒有發出去,所以自然沒收到任何消息。
我把我困在了各種消極的想像里。
那天,貝拉克贏得了幾乎所有選區的支持。
在五彩繽紛的紙屑里,我們開始了下一個四年的白宮生活。
當我回首這整個 8 年的白宮時光,我希望我給美國社會,帶來了一些積極的改變。
我開墾了白宮菜園,在白宮花園里號召孩子們來種菜,讓這里成為他們的戶外教學課堂。
我們還把每次收獲的瓜果蔬菜拿出一部分,捐給白宮附近的慈善機構、流動廚房,分享給那些無家可歸的人。

△ 白宮菜園
我發起了一場運動,名字叫「讓我們行動起來」(Let’s Move!)——力爭解決兒童肥胖症蔓延的問題。

因為全美國有將近 1/3 的兒童,要麼體重超標,要麼患有肥胖症。
我知道要改變這一切是個巨大的挑戰,它牽扯到方方面面。
但我們還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。
全美國三大校園午餐提供商宣布,減少午餐當中的糖分、鹽分和脂肪含量。
我和貝拉克推動的兒童營養法案規定:限制學校的自動售貨機向孩子們販賣垃圾食品,同時資助學校修建菜園。
貝拉克跟記者開玩笑說:「如果我不能讓這個法案順利通過,那我就只能睡沙發了。」
現在,有 4500 萬的美國孩子,每天可以吃到更健康的早飯和午飯,
有 1100 萬的美國學生,每天能抽出 60 分鐘的時間進行體育鍛煉。
類似的,我還推出了「聯合力量」(Joining Forces)計劃,
推動服役士兵、退伍軍人的就業、健康和教育支持。

還有「更高教育計劃」(Reach Higher Initiative),
推動高中學歷的人繼續學習,無論是大學本科、專業培訓,還是社區學院。
還有幫助世界各地的女孩上學的「女孩學習計劃」(Let Girls Learn)……

所有這些,都需要艱辛的努力和精心的組織才能做到。
但我非常清楚,這才是我喜歡的工作。
我站在一個廣闊的平台上,我也終於找到了能充分展示我自己的方式。
可以說,我的白宮八年,過得充實而有意義。
以上這些,就是米歇爾·歐巴馬在《成為》當中所講述的人生故事。
接下來我想跟你聊聊,我對這部回憶錄的感受。
當我讀完這本《成為》,我有這麼一種感覺——
這是一本「正確」的傳記。
我能感受到米歇爾寫作時的真誠。
但真誠有時候就是:我說出來的都是實話,可實話不一定都要告訴你。
這也就使得《成為》並不是一本「知無不言,言無不盡」的傳記。
畢竟書里提到的很多人,現在還生龍活虎、有權有勢。
我們不應該期望太多。
首印 180 萬冊,短短一個月,總銷量超過 500 萬冊。
這已經不是一本書了,而是成為了一個「事件」。

她很清楚任何一句話,對當事人都有可能帶來的「殺傷力」。
所以在書里,甚至包括她個人對特朗普的「批評」,我認為都是相當克制的。
她和歐巴馬的婚姻咨詢過程,書里只寫了開頭(關係比較糟)和結果(關係變好),中間我們所期待的詳細「對話」幾乎沒有。
她和歐巴馬育有兩女,都是通過人工授精的方式,這一點她在書里也沒有正面提及,
前一頁她還在給自己打排卵針,下一頁大女兒瑪利亞就出生了。
而且作為歐巴馬的愛人,她也自然不會貶低丈夫的政治成就。
可歐巴馬的白宮 8 年,究竟功過幾何?只怕還要留給時間去評判。
這麼說來,是不是就意味著,這是一本塵埃未定、又言猶未盡的「半成品」?

我認為不是,它取決於你從什麼角度去理解這本書,去理解這個女人的一生。
我不認為這是一本政治回憶錄,
我認為這是一封寫給每個普通人的信。
貫穿米歇爾·歐巴馬一生的,是一個問題:
你是一個相信自己的人,還是一個相信標準的人?
什麼是標準?就是別人這樣把事情做好了,你去夠到它,你去照著做,你會得到獎勵,你會成為別人眼中「合格」、甚至「優秀」的人。
一個相信標準的人,說到底,是相信他人勝過相信自己的人。
她相信標準,是用來遵守的。
而一個相信自己的人,他覺得外在的標準都不重要:
我能做到什麼,我能做到多好,是我去爭取,是我去定義的結果。
他相信自己,勝過相信標準。
標準,是用來打破的;破了以後,我就是新的標準。
這種對比,就像歐巴馬兩口子。
米歇爾說:你一個美國黑人,你不可能贏的。
歐巴馬說:我不試試,我怎麼知道呢?

對於米歇爾來說,他們二人的區別不僅是成功路徑的區別——
什麼一環扣一環的成功,還是隨性灑脫的成功,這都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,米歇爾從來都不那麼相信「自己」,
她更依賴達到「標準」以後,帶給她的那份安全感。
從幼兒園的時候,一定要念出 white 那個單詞,得到老師手里的金色小星星,
到高中的時候,那個說她考不上普林斯頓的顧問給她帶來的打擊,
到她不相信黑人歐巴馬可以當上美國總統,
到她收不到簡訊,就覺得總統連任一定要失敗的緊張和焦慮……
在有些人的身上,我們會發現:
天生要強,跟不自信,其實一點都不矛盾。
因為要強,是要不輸給那根「標準線」。
但凡有一次,我輸給了「標準」,
我就會立馬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——
我會拷問自己:是不是我還不夠優秀?
就像米歇爾說的:
從一些標準來看,我已經成為一個擁有權力的女性,
但仍然有很多時候,我沒有安全感,我感覺自己被人忽視。
我想,這就是我對米歇爾·歐巴馬做出的評價:
她是一個足夠優秀的人,但她不是天生自信的人。

如果你身邊也有這樣的人,
當你看到他們對自己的苛刻,
當你聽到他們內心動蕩不安的忐忑,
希望你能對他們多一點理解和包容,
因為他們實在是不能輕易就放過自己。
米歇爾說:
如今我已經 54 歲,但我仍在追求進步,我希望未來的我,能夠一如既往,永不停歇。
「成為」(Becoming),是一個進行時,
成為,並不意味著要達到某個位置,達到一個特定的目標。
成為,應該是一種前進的狀態,一種進化的方式,在這條道路上,你看不到終點。
因為成為,就是那一條永不放棄,想要繼續成長的道路。

最後,我想用書里的一個小故事,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:
2016 年 4 月的一天,我和貝拉克·歐巴馬再次出訪英國。
團隊提前告訴了我,各種需要注意的禮節:
下了飛機,我們要先問候王室,然後才能上車,跟他們一起返回城堡。
按照規矩,我要和女王的丈夫——94 歲的菲利普親王坐在前排,親王會親自開車;
而貝拉克要和女王一起坐在後排。
我牢牢記住了這一點,我可不希望像上次見女王那樣,被人指責「失禮」。

可是當我下了飛機,打完招呼以後,先前的計劃全都打亂了。
女王招呼我,跟她一起去坐後排。
我愣住了,我腦子里閃過了無數種想法:
到底應該怎麼做才會更禮貌、更得體——
是應該同意女王的邀請,還是應該堅持讓貝拉克跟女王坐在後排?
女王看著我發呆,她馬上就明白了。
「他們是不是跟你們講了一些規矩?」
女王搖搖頭說:「那都是胡扯。你願意坐哪兒,你就坐哪兒。」(That’s rubbish. Sit wherever you want.)

她瞬間化解了我內心所有的大驚小怪,和沒有必要的擔心。
是啊,你想坐哪兒,你就坐哪兒。
你不需要成為一個高高在上的伊麗莎白女王。
你是你自己的王。
(此文來源於網路,如有侵權立馬刪除)






 專注在 兩性、愛情等領域
專注在 兩性、愛情等領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