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,城外的人想沖進去,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」。
這是楊絳女士寫在《圍城》扉頁的一句話。
無論你混的是哪個圈子,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擁有過一番經驗和作為,每每回望時總會難免發出類似的感慨。
當在《幻樂之城》中偶然瞥見劉文傑時,我再也想不出比這句話更適合形容他的其他文字。

劉文傑他是誰?我想十有八九的人都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。
寄蜉蝣於天地,渺滄海之一粟。
他是出道十年的新人,也是在樂壇沉浮十年的舊人。
歸根結底,他更像是一個陌生人。
▽
劉文傑的圍城,就是他的身份標籤。
如今他的身份,是曾經風靡大街小巷的搖滾樂團「信樂團」現任主唱。
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背後,是盛名之下的難言之隱。
華語搖滾音樂文化中,「北漂」是提及頻率極高的關鍵詞。
與很多前輩同仁們的經歷相似,劉文傑在開始的開始,只是一名懷揣音樂夢想的普通年輕人,只身來到北京投奔虛無縹緲的理想烏托邦。
某種意義而言,他算是半個天才。他於體育院校中選擇半路出家,能踢得一腳好球,卻在射門、傳球與盤帶的間歇始終放不下耳畔的音符。
萬幸,他唱得還算不錯。
至少每一個在北京聽過他唱歌的人都這樣說。
《北京愛情故事》里對於北漂青年下過定論:
你看這路上形形色色匆匆忙忙的人,他們大多數都是為了生計而辛苦的奔波著,可是他們中間不是誰都有機會來真正改變自己命運的。
外人看來,劉文傑擁有著上天賜予的好運氣。
剛剛來到北京不久的他,恰恰遇到信樂團歷經主唱單飛之後的回歸主唱選拔。
幾個晃神,如夢似幻,竟然在擊敗了茫茫多的強力競爭對手,拔得頭籌完成入主。

▽
夢境,畢竟是大腦錯覺堆疊的產物。
劉文傑一度以為自己被從天而降的餡餅砸中,此後將在演藝圈坐上雲霄飛車保持上升,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收割理想。
然而這個夢,其實才剛剛開始。
理想很豐滿,現實很骨感。落俗的流行語,也是真實的心聲。
與信樂團此前專輯武裝到牙齒的宣發配備相比,劉文傑所擁有的僅僅是小米加步槍。他原本有著一整套的完整生涯規劃,直到主唱身份加身的頃刻間崩塌。
就像刮獎中了五百萬美金,連怎麼花錢都想好了,主辦方卻說:這張彩券作廢。
▽
桎梏於樂隊常年遺留下來的舊傳統,劉文傑發現,樂隊的航向與自己這個掛名「船長」的初心有著不小出入。身為年齡最小的成員,他面對幾個老大哥顯得人微言輕。
現在的樂團,是他心目中崇拜的那個信樂團嗎?
你總是很難改變一個人的習慣,更何況這是一群人。
原來信樂團早已被公司的全方位立體式包裝,外加他人承包詞曲創作給填飽了肚子,就更難以接受劉文傑獨立創作的意圖。
那麼劉文傑在信樂團的話語權到底低到什麼程度呢?
從內心到外表的被迫融入。
多年馳騁在綠茵場,日常生活中的他只喜歡休閒寬鬆的穿搭。
但他幾乎每一次站在舞台、每一次進棚拍照,都是黑色緊身褲。
別問,沒有為什麼,因為別人都是一水黑色。

音樂的世界更新迭代太快了,生物學已無數次證明過用進廢退的道理。
坐在功勞簿上吃老本,金山銀山也揮霍不了幾年。
一個聽起來難以置信的數字:
劉文傑在信樂團的十年,僅製作過一張像樣的專輯。
與硬件配備嚴重不相匹配的,是內部和外部賦予的雙重壓力。
開什麼玩笑,你可是信樂團的主唱啊。
明明是獨角戲,為何卻不配有姓名。
昔日輝煌與今日的失落形成了難以逾越的落差。
但凡《死了都要愛》、《離歌》、《海闊天空》還在被傳唱,人們回憶起來就永遠只能想起其蘇見信。
至於劉文傑,誰記得?誰認可?誰信服?
五年前他曾參加《中國最強音》,把姿態放到最低。
當他向坐在評委席的四個導師做自我介紹時,那句「我也是個藝人」說得似乎並沒有太多底氣。

外出商演的舞台,他面向熱情洋溢的觀眾聲嘶力竭飆起高音。
最前排有狂熱觀眾拼命扒向舞台,只為看清他的面孔。
山呼海嘯的聲音中依稀能夠聽到:蘇見信,我愛你。
他苦笑。你說是,那就是吧。

事隔十年,人們提起劉文傑總是說:
信樂團的主唱,新任的。
真相是:他無論站在任何角度去評價,都已算不上新了。
其實他比前任呆在信樂團的時間還要久。
其實他也沒那麼年輕了,盡管臉上還是帶著幾分倔強。
▽
心理暗示是最可怕的情緒,它可以風輕雲淡摧毀掉任何努力與積累。
在網易雲音樂的評論區,劉文傑的歌曲下方,這樣的評論隨處可見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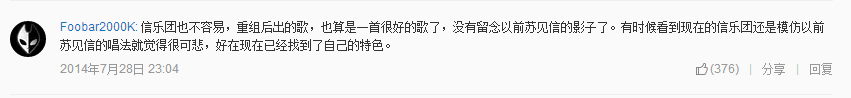
沒有人了解、更沒有人願意了解劉文傑。
沒有人知道,劉文傑曾擊敗多少對手,方能站在如今這個看似風光的位置。
沒有人知道,劉文傑也擁有著一把燙金般的嗓子,音域比《死了都要愛》的最高音還要高出三度,現場穩定性讓所有聽過現場的觀眾嘆為觀止。
你可能很優秀,但你不是他,所以我們就是不喜歡你。

他是出道十年的新人,也是入主十年的新主唱。
他還是會在音樂道路上默默堅持。
心尖有雨,輕輕撣去便是。
回首過往,還是那個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




 專注在 兩性、愛情等領域
專注在 兩性、愛情等領域